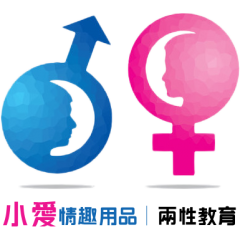你的妻子跟一個已婚男人跑掉了,沒有哪種情感會像此時男人的情感那樣的吧。
那是在1989年,在一個炎熱的夏天的晚上,我下班回家卻看到了一幅很讓人惱火的戲劇性場面:在我們單人房住宅里,我妻子的大部分財物都不見了。那隻貓也不見了。她之前已經去到了車站。
稍晚些,電話響了。
我妻子就這麼說了一句:“我需要時間想想。”
令人痛苦的八天過去了,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來信——沒有回信地址——在信中,她表達了她對一位已婚男人的愛慕,這個男人是她看管的酒吧的常客。我們結婚兩週年紀念的六個星期前,我們的婚姻結束了。
當然,我感到很震驚,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試圖重新建立我的生活。我開始去看臨床醫生。我閱讀自助書。我迅速地進行一個狂熱的房屋革新項目,計劃把我的住宅從一個愛巢變成單身公寓。
我也聽到很多女性聰明的勸告。我與她們分享。我聽了。我哭了。
我對我的女性團隊陪伴我走過這感情的雷區是很感激的,這個團隊裡有我的前女友薩利,同樣離婚的我的鄰居林恩,甚至我的媽媽,在生活中他們都會直切入正題地跟我聊。
我工作的雜誌社老闆巴里跟我說:“只要你把所有煩惱的事放在一起就可以從中脫身了,只有你準備好了才可以回來。全薪。”
我的另一位同事,同時也是廣告銷售行業的副主席說:“你想去哪?拉斯維加斯?洛杉磯?我預定你的機票——我會把它放在我辦公室的錢箱上。”
“女人照顧,男人看管”這一句格言適用於從家庭動力學到會議政治學的方方面面。然而當說到關係這方面的時候,這個治百病的藥的效果並不好。當我們順著本能去做出正確的改變的時候,男人們經常被勸告去沉湎於對關係的微量分析,這個分析甚至會奧普拉都感到筋疲力盡。
但是在那個夏天,我很有勇氣地走了下去,每當我感到難受的時候我就去找我的男性朋友。他們並沒有什麼探通術,我的女性好友們也有很緊張的日程安排,他們卻在這個時候滿足了一個更為緊要的需求:感覺到了我已經控制好了自己。因此,我很感激,甚至很放心,因為我的朋友們在一直支持我和引領我重新上路,他們似乎對這個比起我那些受到傷害的感情故事來說更感興趣。他們的陪伴讓我感到很舒服。
與此同時,我發現了一些別的東西:一種隱藏的兄弟情誼在我的朋友圈外出現。出租車司機,服務員,甚至在我住宅內外遊逛的一群女人都似乎很熱衷於與別人分享他們自己的故事,我跟他們感覺是在同一戰場的老兵。這些新的顧問團隊都挺有幫助的,一般我都不知道他們的名字——讓我們面對吧,同情是個很美妙的事物。
“你認為你這就算糟糕了?先聽聽我的故事吧!”我住宅的牙買加油漆匠在聽到我悲傷的故事之後這麼跟我說,然後他跟我講述了一段發生在家庭裡的混亂的事,這事使得我的故事聽起來象“脫線家族”的一段插曲。
我記的最清楚的是他剛會走路的兒子——他所描述的與我相同的破裂家庭的產物——在我的起居室的地板上很開心地玩著油漆罐。
我在想:“如果這個傢伙能跟孩子一起度過這個痛苦的時光,我肯定也能。”
自從我的妻子離開我後,我第一次感到了希望在閃光。
我的朋友丹最終讓我走上了恢復的道路。跟我一樣,在我的危機爆發的幾個星期後他的妻子也離開了他,所以我們成立了一間俱樂部,我們把它叫作“孤獨之心”俱樂部。每個星期四的晚上,我們都會在一間意大利飯館吃些麵食,聊些傷心的事。在食物上來之前,我們都會分享對近來緊縮政策的普通看法。接著我們會重點談談未來——無論我們在比賽誰會第一個跟女人上床還是無休止地討論棒球季度賽的第二節。
女人經常說:總是討論性和體育運動代表著男人的淺薄。但是對我和丹來說,這些話題有更深的含義:它們讓我們憧憬著某些東西。最後,我想,我們是個摔交組,共同對付著一個敵人:停滯不前。
“孤獨之心”俱樂部在成長著。處於婚姻危險期的斯圖和沃爾特加入到了我們的行列,他們在家遭受的令人吃驚的多次責罵讓我們例行公事般地感到目瞪口呆。極少有人提供說明性的建議,我們都只是聽著。很好奇地,我們四個都是“好人”,我們談論有關關係方面的議論,而且真正付出努力去建立一種女性雜誌所說的不存在的敏感關係。然而,不管怎樣,我們都喝醉了。
幾個月後,俱樂部開始解散了。我遇見了一位女人。丹去了加利福尼亞州。斯圖和沃爾特漸漸地開始他們緩慢而悲傷的離婚進程。
.現在距“孤獨之心”俱樂部的最後一次會議已經有16年了。我很高興的跟大家說,四個俱樂部的成立人員現在都結婚了——我們當中的三個有了孩子。我不敢說我們各自的快樂結局是否是我們在圓桌中建立的任何關係的直接結果。但是可以說,沒有那個夏天那些特殊朋友的真誠陪伴,我一路上將會走得更慢——也走得更孤獨